生沅陵 归长江:
诗人朱湘的悲情人生
作者:周万水
他被文豪鲁迅先生称作“中国的济慈“。他一生毁誉参半,16岁上清华,19岁被开除,他曾经才华横溢,独步文坛。他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历程中重要的诗人,却孤傲不群,行事乖张怪癖,注定一生悲情。读书期间,他对学位不屑一顾,曾宣称:“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他就是出生于湖南沅陵,被称作民国“清华四子”之一的中国现代诗人朱湘。

诗人朱湘
1904年春,湘西沅陵。沅江畔的辰州府被一层薄薄的、银灰色的寂静笼罩着,随着一阵婴儿清脆的啼哭声,湖南辰州盐巡道朱延熙的第五个孩子出生了。朱延熙很高兴为这个男孩取名为“朱湘”,字“子沅”。“湘”与“沅”楚地两条河流的名字,在汉字系统中,其意义都是具有唯一的。沅水逶迤,岸芷汀兰,这里有屈子行吟的忧愤,有从香草幽泽飘来的《楚辞》的芬芳。从此湘沅的波光与离骚的遗韵,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诗行中有了不绝的回响。1904年5月20日(农历四月初六)这一天,似乎注定了朱湘一生的才华与孤傲,也注定了二十世纪一个伟大诗人的困顿、绝决和无力抗拒的宿命。
这哭声里包裹着的那个小生命日后所有的热烈与孤愤、绚烂与决绝。这一天,沅江水无声流着,仿佛就已经开始默默计算,从这个春日开始到之后三十年一个寒冷的冬晨,那个沉入长江的诗魂与时间的距离。谁又能知道,那一声啼哭里包裹着的那个生命日后所有的热烈与孤愤、绚烂与决绝,最终将朱湘这个名字化作中国新诗银河里,一颗光芒凄艳而短促的寒星。
朱湘的父亲朱延熙,是安徽太湖人,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光绪12年(1886)中一甲进士,其胞兄朱延薰亦为同榜进士。兄弟同榜,极为少见,光绪帝曾特赐“甲第逢春”金匾一块。入仕后先后获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修纂,后又任陕西乡试主考官、江西学台、湖北延巡道、湖南关道、臬司、提学、盐巡道等职,官居二品。因为政清廉,才高绩显,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赏识。朱延熙发妻余氏,生长子朱文寅,未成年即早逝。后经张之洞牵线,将其侄女(湖北候补知府张之清之女)续弦于朱延熙。张氏生有四子二女。四子分别为文长、文良、文祜、文同(朱湘)。朱湘的母亲虽没留下姓名,但据说“性温且敏,通书史,解音律,而尤精于琴操之学”。

诗人 朱湘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秋,奉调湖南沅陵,任辰州盐巡道。盐巡道是清代负责盐务管理与监督的官员或职掌,职责包括盐政巡查、税收监管、盐务稽查及协调盐政事务。朱湘正是在其父任辰州盐巡道时,诞生于辰州府治沅陵的。
关于朱湘的生平信息,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生于1904年10月5日,二是生于1904年5月20日(农历四月初六),然据《朱氏宗谱》(白鹿堂木活字本,民国六年修)记载,朱湘谱名“文同”,生于光绪三十年甲辰四月初六酉时,即1904年5月20日。该家谱为朱湘生前所修,具有较高的史料可信度。关于朱湘离开沅陵的时间也有多种说法,可信的说法应该在1904年7月,因为此时,朱延熙已调任湖南盐法道兼海关道,据此判断,朱湘一家也应该迁居长沙。这时的朱湘不足半岁,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朱湘的作品中没有任何关于沅陵的记忆的原因吧
虽然朱湘好奇的眼神还未认真打量这片神奇的山水,但是沅陵,这个被青山与流水相拥的名字还是融入了他的血液与骨髓。朱湘的字叫“子沅”,若干年后,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取名为“小沅”,就是对沅陵这“衣胞之地”灵魂深处的依恋。在辰河的浸润中,朱湘第一次呼吸便有了楚地沉郁和漂泊的基因。清冽的沅水带着西南山野的浪漫,也带着一份天然的孤僻。这长河,似乎早早地在朱湘生命的底色里,掺入了清冷与桀骜。
随父母迁居长沙后,天赋极高的朱湘,在贤淑高雅的母亲的精心抚育下,其艺术细胞得以充分激发。但不幸的是,朱湘4岁时生母却因病去世,忙于政务的父亲也极少能够关注他内心世界,无人能够填充母亲去世后在他心中形成的巨大空白。后来,父亲又续娶继母冯氏。长期的冷清孤寂,对朱湘孤独、自卑、敏感、落落寡欢的性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联。

失去母亲时,朱湘才4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对他整个人格结构和性格的塑造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决定性的。弗洛伊德说:“一个人的童年将影响他的一生”。4岁正处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关键期,母亲通常是其情感依恋的“安全港湾”。母亲的骤然离世,意味着这个港湾永久性地缺失。这种缺少会带来本能上的被抛弃感与不安全感。由于年龄尚小,他无法理解和处理这种巨大的丧失。这种原始的恐惧和焦虑便被压抑进潜意识,成为其日后朱湘敏感、多疑、自卑、缺乏安全感的原点。很多年后,朱湘写诗,写江上的船,写天上的月,写得清冷、孤绝、一字一顿。他的诗歌中那种对理想之美的执着、对孤独的深刻体验,以及最终走向毁灭的决绝,都可视为其内心世界的投射。可以说诗歌是朱湘疗治童年创伤、构建理想化精神家园的唯一途径。许多人说他的诗里少了点温暖,但或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四岁那年,深宅大院里那忽然而至的孤立无助,像一缕缕凉飕飕的风,一直吹到长江边,吹到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就这样,失去母亲的朱湘仿佛像一只风筝,在空寂的天上飘摇,虽然衣食无忧,但没有了母亲的牵引,所有的日子都无异于流浪。这期间,他唯一爱好就是一个人躲在屋内看书。看诸如童话、侠义小说之类的读物。尽管不大懂,但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父亲对他还是很钟爱,教他识字、写字,还为他专门延聘了私塾先生对他进行启蒙教育。但幼时的朱湘最刻骨铭心的感受除了孤独还是孤独。他很少接触的人,执拗、不合群,经常独处一隅默默看书,被家人唤作“五傻子”。后来,朱湘在《我的童年·读书》一文中这样的描述:“这是在离家有几里远的一个书馆里的事情。有一次,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馆里,心里忽然涌起了寂寞、孤单的恐惧,忙着独自沿了路途,向家里走去……”
宣统元年(1909),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社会动荡不安,民众与西方列强的矛盾也十分尖锐,朱湘的父亲署理湖南按察使身处社会矛盾的旋涡之中,身心俱疲,于宣统三年(1911)辞官回乡。回归老家后,朱湘继续在村塾读书,习读了《龙文鞭影》《诗经》《四书》《左传》等等,从而具备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

朱湘与夫人刘霓君
一九一四年,朱延熙去世,朱湘成了孤儿。那年他十一岁。
父亲没留下多少遗产,只将他托付给了大哥朱文焯。大哥是堂房过继来的,与朱湘并非同胞,长他二十六岁。于是朱湘跟着长兄去了南京,进入江苏省立第四师范附属小学读书。长兄性情暴躁,稍有差错,便要挨打。小学毕业后,朱湘考入南京工业学院预科。
在南京的那几年,除了读书,日子仍是孤寂的。幸好,他的二哥也在南京。二哥朱文长,与他为一母所生,虽然平素见面的日子不多。但朱湘的二嫂薛琪瑛,却是照进他灰暗生活里的一束光,是他少年时代少有的暖意。
薛琪瑛出身无锡名门,是近代中国外交家、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起者薛福成的孙女。她受过良好教育,曾留学法国,通晓英、法、拉丁语,是最早用语体文翻译西方剧作的翻译家之一,译过王尔德的《意中人》、格莱亨的《杨柳风》、奥斯丁的《婚姻镜》。她有旧学的底子,又有西学的眼界,那些年,朱湘从薛琪瑛那里接触到西方文学和戏剧,也渐渐对西方语言有浓厚兴趣。那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都渗入了他的诗歌创作里,形成了东方古典意象与西方诗律相结合的冷峭幽深的艺术风格。
一九一八年,朱湘十五岁,从南京工业学院预科毕业。他去上海青年会补习英语,之后报考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次年,十六岁的朱湘被录取。清华是用美国用庚子赔款兴办的,招收各地优秀学生,教学以英语为主。朱湘插入中等科三年级甲子班,同学中有周培源、梅汝璈、冀朝鼎等人。
一九二一年九月,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第一首诗《死》。后来加入清华文学社,与梁实秋、顾毓琇、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等人同社。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和他,并称“清华四子”,取子沅、子离、子潜、子惠之号,是当时诗坛上最活跃的年轻人。
或许,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朱湘是一个才华超群、前途无量的诗人,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剧情却开始反转。童年时代加持在诗人身上性格与心理特质,最终还是推着朱湘走向自己不可抗拒的宿命。
朱湘是一只孤鹤,硬颈昂首于乱世的浅滩。他高傲不群,不愿在泥泞中啄食。为了心中的自由,他注定一生要与一切束缚和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为敌。

朱湘一家人合影
这一切都开始于清华园。那时的朱湘还未被“孤僻”二字钉死,他只是个沉浸于诗艺的年轻才子,“清华四子”,在《小说月报》上初试才情,名气斐然。然而他性格中那近乎洁癖的耿直,让他无法忍受刻板的校规。他抵制早餐点名,累积记三次大过被开除时,竟在园中“若无其事地徘徊”。在他眼中,人生是热辣辣的奋斗,而清华“只有钻分数的单调与虚假”,这种对世俗秩序的藐视,是他后来所有悲剧的底色。
当他在文坛崭露头角、出版《夏天》与《草莽集》时,爱情也悄然而至。他本反感包办婚姻,却爱上了那个叫刘霓君的女子,那是父亲指定的姻缘。婚后生活甜蜜,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写下的九十封情书,编号排列,情意缱绻,汇成一本《海外寄霓君》,那是他一生中最柔软的时光。然而,这份柔软却包裹在他浑身带有强烈自卑的刺壳里。在美留学的时候,因有教授将中国人比作猴子,他愤然离校;后又因被人怀疑借书未还,加之有美女不愿与他同桌,他再次拂袖退学。他说:博士学位谁都能拿,但诗非朱湘不能写。
1929年回国,他任教于安徽大学,月薪三百元,本可安身立命。但因校方将“英文文学系”改名“英文学系”,这一字之差触动了他病态般的敏感神经,他竟大骂教师出卖智力如同妓女出卖肉体,又一次愤然辞职。他骂胡适的诗“内容粗浅,艺术幼稚”,讽徐志摩为“瓷人”,跟好友闻一多翻脸,在文坛四处树敌。他太需要尊严,以至于把整个世界都当成了假想敌。
他高傲的骨子里充满对权威的蔑视。清华拟聘请现代评论派的头面人物陈西滢来学校教授英文,朱湘得知后轻蔑地说:“他也配来清华教书?只有我来教他才差不多。”一句话果然让陈西滢真知难而退。

朱湘与刘霓君
可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诗意终究是虚幻的存在。他失去了很多工作的机会。他是诗国的王者,却是生活里彻底的败将。生计的困顿,磨损着诗人的尊严。他手中那支曾织就锦绣音节的笔,却写不满人间最寻常的柴米油盐。他与霓君的孩子因病夭折,那幼小的生命哭了七个昼夜后死去,夫妻间曾经浪漫的温情也随之冻成冰窟。他不再是那个写情书的浪漫丈夫,而是成了一个被柴米油盐逼到墙角的落魄书生。朱湘彻底绝望了,他开始自言自语地说:“我真傻呀!我真的该去死了吗?
1933年12月5日,在上海驶往南京的轮船上,朱湘带着一瓶酒、一包妻子爱吃的饴糖,以及两本书——一本《海涅诗集》一本他自己的作品,他高声朗诵海涅的诗,纵身跃入冰冷的长江。江水吞没了那个孤傲的背影,也吞没了现代诗坛的一颗寒星。他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叹:朋友、性、文章这三件大事,因他那不容沙子的孤僻,最终只余下文章,陪着他沉入江底。
一个天才诗魂就这样陨落了,这一年朱湘年仅29岁。
1925年,他曾写过一首诗《葬我》,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葬我在荷花池内,
耳边有水蚓拖声,
在绿荷叶的灯上,
萤火虫时暗时;
不然,就烧我成灰,
投入泛滥的春江,
与落花一同飘去
无人知道的地方……
从沅水出发,到长江陨落,两水茫茫,朱湘完成了对自己精神与肉身的最终定义。他的一生是一场短暂而漫长的漂泊。他的诗,是两水之间一座灵魂的桥梁,玲珑,冷峭。那纸页间的韵律,总似带着深深浅浅江流的呜咽,泛着永恒的、悲剧性的波光。他的诗,是雕琢的玉石,有着济慈般对美与音韵的极端苛求,却又在格律之下,藏着一个忧愤而敏感的灵魂。鲁迅称他“中国的济慈”,这赞誉里,或许也听出一丝对其命运隐忧的叹息——济慈,亦是早夭的天才。
如今,沅陵的青山依旧,只是那个从沅水岸边出走的诗魂,早已顺流而下,汇入了东方那片无言的、深蓝色的海洋。
朱湘终究还是回去了,以一种凛冽的方式,与他追随的世界融为了一体。
他的故乡究竟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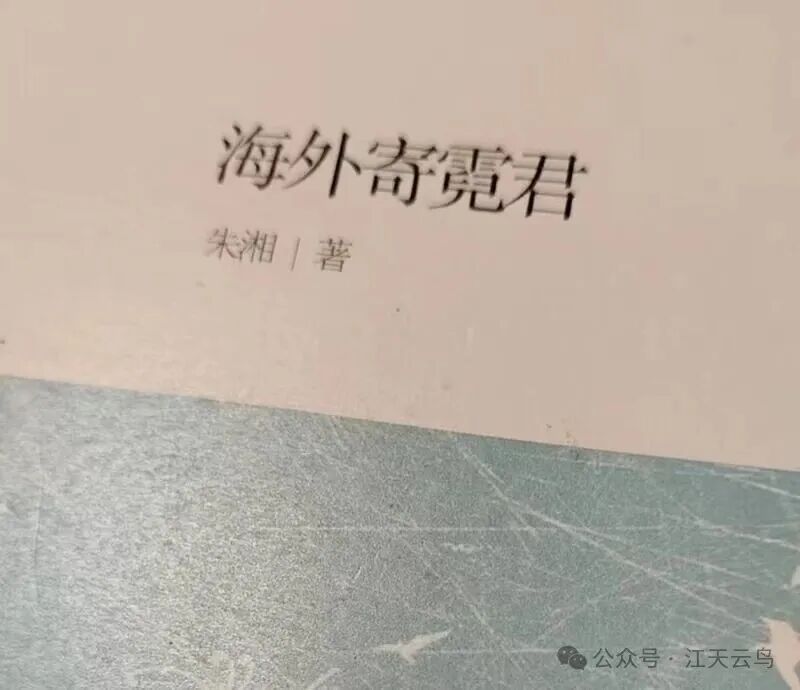
朱湘书信集《海外寄霓君》
附:朱湘诗二首
《致一多基相》
我是一个惫殆的游人,
蹒跚于旷漠之原中,
我形影孤单,挣扎前进,
伴我的有秋暮的悲风。
你们的心是一间茅屋,
小窗中射出友谊的红光;
我的灵魂呵,火边歇下罢,
这下是你长眠的地方。
《残灰》(节选)
炭火发出微红的光芒,
一个老人独坐在盆旁,
这堆将要熄灭的灰烬,
在他的胸里引起悲伤
火灰一刻暗,
火灰一刻亮,
火灰暗亮着红光。
童年之内,是在这盆旁,
靠在妈妈的怀抱中央,
栗子在盆上哗吧的响,
一个,一个,她剥给儿尝-—
妈哪里去了?
热泪满眼眶, 盆中颤摇着红光。
到青年时,也是这盆旁,
一双人影并映上高墙
火光的红晕与今一样,
照见他同心爱的女郎--
竟此分手了,
她在天那方?
……
来源:江天云鸟
编辑:唐圣利